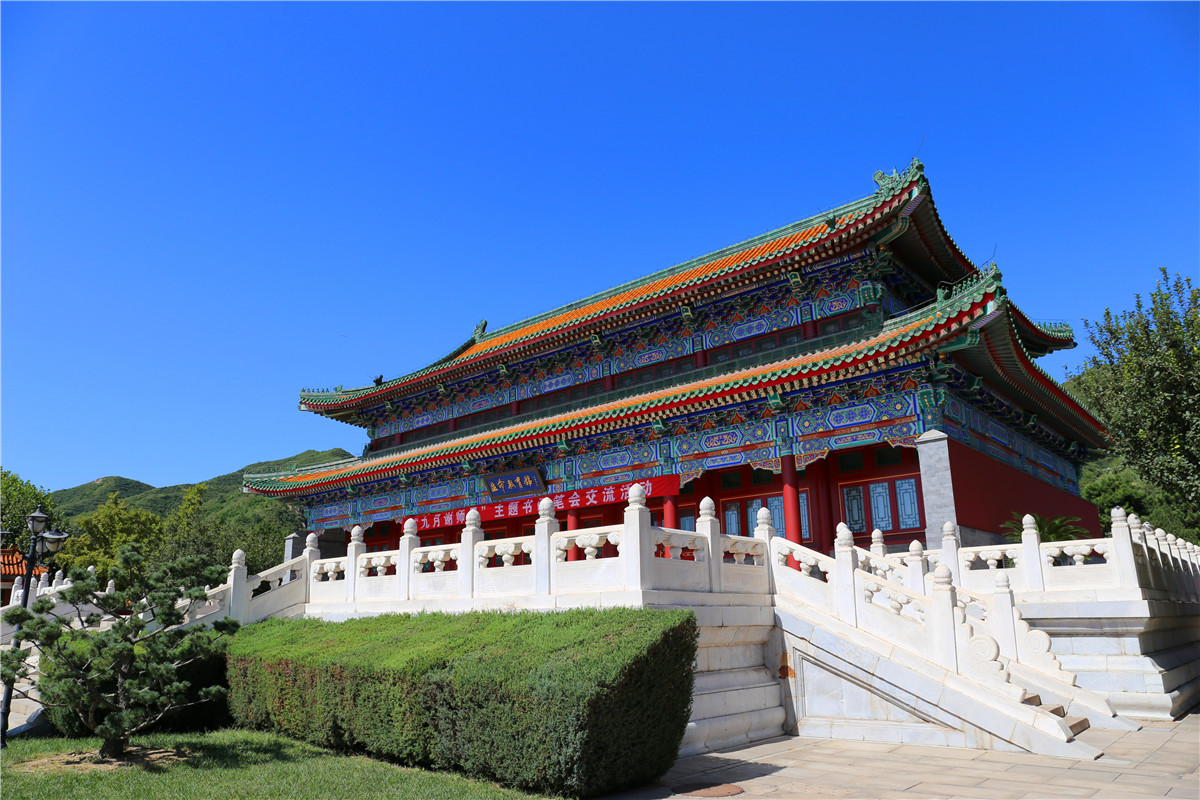北京的秋总是来得早,昌平山脚下的华夏陵园刚入九月就浸满了松针的苦香。清晨五点,住在附近的王阿姨会绕着陵园的围墙走三圈——不是特意要做什么,就是觉得这园子里的风比别处暖些,像裹着些没说出口的牵挂。园门开着一道缝,管理员老张正蹲在台阶上擦铜牌,看见王阿姨就笑:“早啊,又来陪孩子们?”王阿姨点头,目光掠过里面整整齐齐的石碑,轻声说:“昨天梦见我家那口子了,他说这儿的松树长得比当年密。
常有人问“华夏陵园有多少烈士”,老张摸出胸前的钥匙串——那上面挂着个褪色的红军像章——说:“登记本上记着一千三百七十二位,可还有些没名字的。”他指着东边的“无名烈士墓”,水泥碑上没有名字,只有“抗日英烈永垂不朽”八个红漆字,“当年打扫战场,有的战士连块能证明身份的布片都没有,只能合葬在这里。”这些名字里,有1948年解放北平牺牲的通讯员小周,1951年在朝鲜松骨峰战斗中牺牲的机枪手刘柱子,2020年在抗洪中被洪水卷走的消防战士陈默,还有2022年牺牲在维和任务中的军医林晓雨。“你看这碑上的日期,”老张摸着一块新刻的石碑,“上个月刚添的,是位缉毒警察,牺牲时才26岁,家里人把他的警号刻在了名字下面——007896,说这样他就还是穿警服的样子。”

李阿姨的儿子李刚在2015年的一场火灾中牺牲,那年他刚满22岁。每个月的15号,李阿姨都会坐最早的公交来,带一盒剥好的橘子——那是李刚最爱吃的,橘瓣摆成小小的堆,放在碑前。“刚子,昨天你表妹考上大学了,学的消防工程,跟你一样。”她用指尖摩挲着碑上的名字,“你看,这字儿又亮了点,是上周来的小学生摸的,他们说长大了要当像你这样的人。”旁边的石碑是位无名烈士,每年清明都会有个穿旧军装的老人来,把一束野菊花放在碑前,不说别的,就坐着抽根烟。老人说,1947年他跟着部队打张家口,被敌人的子弹追着跑,是个穿灰布军装的战士把他按在沟里,自己却中了枪。“他倒下去的时候还抓着我的胳膊说,‘快跑,别回头’,我连他叫啥都不知道。”老人的手背上全是老年斑,像一片风干的枫叶,“现在我走不动了,可我儿子会接着来,我孙子也会来。”
周末的陵园最热闹,不是吵闹,是热气——穿着校服的学生排着队进来,手里捧着自己做的白花,纸折的百合、玫瑰,还有用银杏叶做的书签。志愿者小张举着扩音器,声音放得很轻:“这位是陈默叔叔,他牺牲的时候,怀里还抱着个三岁的小孩;这位是林晓雨阿姨,她在非洲救了二十多个当地孩子……”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拽了拽小张的衣角:“叔叔,烈士叔叔们会看见我们吗?”小张蹲下来,指着天上的云:“你看那朵云,像不像陈默叔叔的消防帽?他们就在云里看着我们,看我们上学,看我们吃好吃的,看我们长大。”学生们对着石碑敬队礼,红领巾在风里飘得老高,像一面面小小的红旗。
其实关于“有多少烈士”,答案从来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。它是松针里的香气,是李阿姨的橘子,是老人的野菊花,是学生们的队礼。这些烈士从来没有离开,他们变成了风,变成了光,变成了我们每一次面对选择时,心里那句“我愿意”。站在陵园的台阶上往远处看,山脚下的村庄飘起了炊烟,马路上的汽车鸣着笛驶过,幼儿园的孩子在唱《小星星》。风裹着松针的香气吹过来,像有人轻轻拍了拍你的肩膀——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