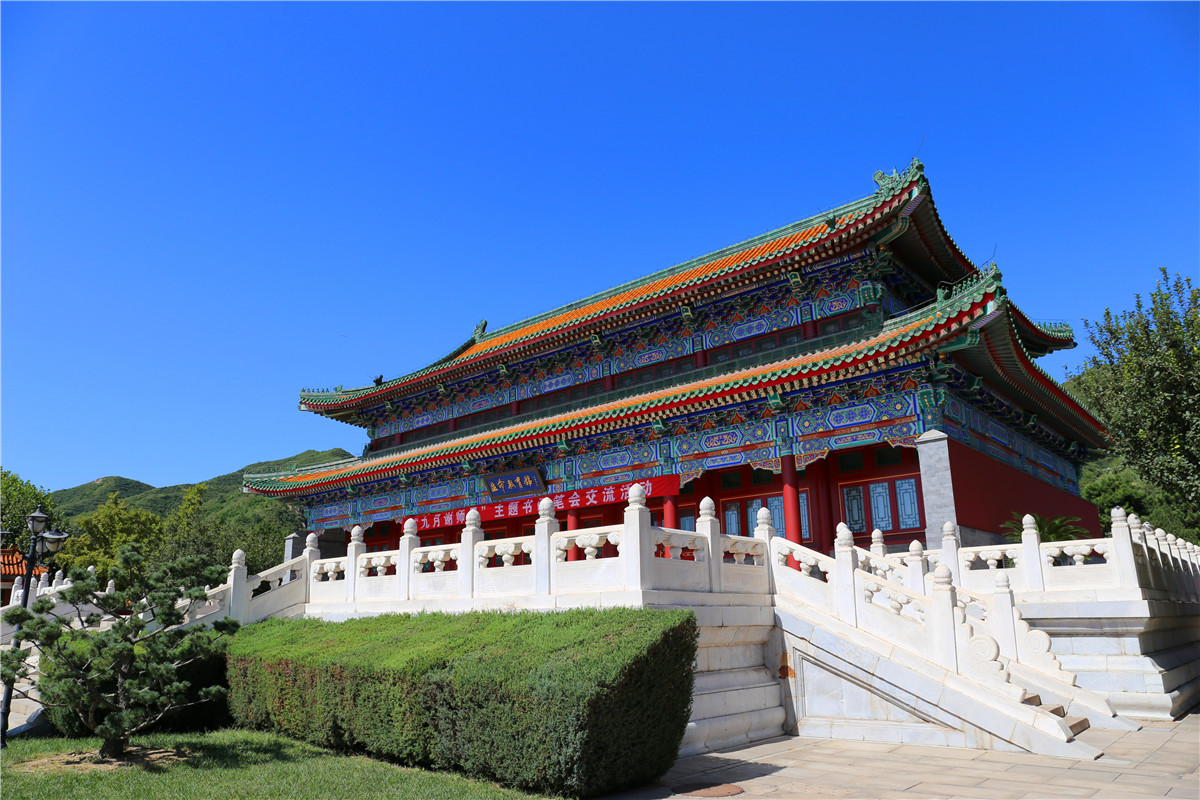入秋后的外桥公墓浸在淡金色的阳光里,沿台阶往上走,道旁的香樟落了一地碎叶,踩上去沙沙响。我扶着碑歇脚时,旁边一位擦墓碑的阿姨忽然问:“姑娘,你知道这公墓到底始建于哪年不?”她的问题像片小石子,掉进我心里——来之前我查过资料,可那些干巴巴的数字,总不如眼前的烟火气来得真切。
后来我抱着笔记本往巷口走,路过社区居委会时,遇到了墙根下晒太阳的张阿公。他是土生土长的外桥人,今年八十七岁,听说我问公墓的年份,摸着下巴上的白胡子眯眼想了半天:“我小时候跟着爹去上坟,那时候不叫公墓,叫‘外桥义地’。爹说,民国十八年发大水,滁河决堤冲了三个村子,好多人没了家,连埋人的地方都没有。乡绅李伯仁看不过去,找了几个商号凑钱,买了老桥西边的坡地——就是现在公墓的前半部分。”张阿公伸手比了个“十”字,“那时候没有碑,就插根竹片写名字,坡顶还搭了间草棚,给守墓的老王住。”为了验证他的话,我后来翻到区档案馆的民国档案,其中一份1934年的《江浦县乡绅募捐清单》里,果然有李伯仁的名字,后面跟着“捐银洋二百元,用于购置外桥义地”的备注。原来县志里写的“民国二十三年”是正式登记的年份,而张阿公说的“民国十八年”,是义地最初的雏形——那些埋在土里的竹片,比纸上的数字更早见证了这片土地的温度。
外桥义地真正变成“公墓”,是在解放后的1952年。我在公墓管理处找到退休老管理员周叔,他掏出本破破烂烂的《公墓登记册》,纸页边缘卷着毛边,上面用蓝墨水写着:“1952年10月,将外桥义地及周边零散墓地整合,命名为‘外桥公墓’,划归县民政局管理。”周叔用指尖点着第一页的登记项:“你看,第一个入葬的是陈桂英老太太,家住外桥村三队,死因是‘年老寿终’,碑号是东一区三号。”他抬头望着窗外的松树,“那时候我才十五岁,跟着爹来帮忙,记得第一次立水泥碑时,好多老人哭着摸碑面,说‘这石头比竹片牢,再也不怕雨淋了’。”六十年代,公墓种了一圈马尾松;七十年代加了红砖围墙;八十年代铺了柏油路,还建了公共卫生间;九十年代又扩了二十亩,盖了骨灰堂——每一次变迁都刻在周叔的记忆里,像棵树的年轮,一圈圈绕着中心的“根”。

现在的外桥公墓,早已不是当年的土坡地。清明时台阶上会排起长队,年轻人抱着百合,老人提着纸扎的房子,孩子们举着小风车跑在前头。我曾见过一位穿汉服的姑娘,在碑前摆了杯桂花酒,轻声说:“奶奶,今年我考上你当年想上的大学了。”也见过几位老工友,围在一块碑前抽烟,说:“老周,当年你欠我的红烧肉,下次带过来啊。”这些瞬间让我忽然明白,人们问“始建于哪年”,其实问的不是一个数字——而是想知道,这片土地上埋着多少人的故事,藏着多少代人的牵挂。就像张阿公说的:“你看那棵老槐树。”他指的是公墓西北角的古槐,树身要两个人合抱,枝桠铺得像把大伞,“我小时候它就这么粗,现在还是这么粗,可树底下埋的人,换了一茬又一茬。”风掠过槐叶,沙沙响,像有人在说悄悄话——那些关于年份的疑问,最终都落在了每一片叶子里,每一缕风里,每一个来祭扫的人的心里。
SE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