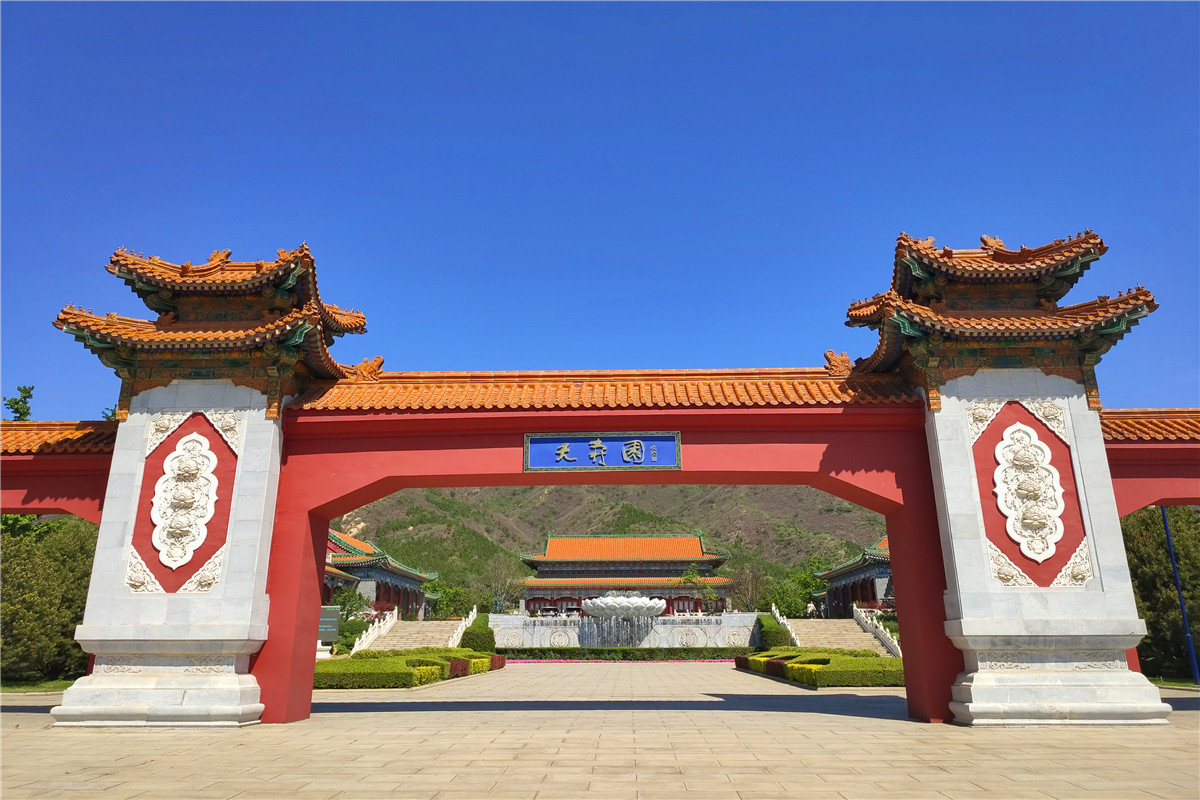沿着北六环往西北走,过了温榆河支流的小木桥,佛山陵园的入口就裹在一片银杏林里。十月的风把叶子吹得黄亮,像撒了满路的碎金,连风里都飘着银杏的甜香——两排银杏树像守着门的老伙计,枝桠碰着枝桠,像在小声打招呼。穿藏青外套的老人蹲在第三排墓碑前,用旧手帕擦碑身,动作轻得像抚过爱人的手背,擦完摆上一束白菊,花瓣上还凝着晨露,是他早起绕了三条街从花店挑的。
佛山陵园的好,是藏在“园里有园”的心思里。进门往右拐,穿过青竹掩映的小径就是梅园区,竹影扫过碑面,有块碑上刻着“梅妻鹤子”,旁边摆着半块凉透的梅花糕——是巷口阿婆送的,她说逝者生前总在下午三点来买,“现在我每周来摆一块,就当他还在”。兰园区的青竹长得密,风穿过去时像吹起一串碎笛,有位老先生坐在石凳上拉二胡,琴身泛着旧旧的光,他说“我爸生前爱拉《良宵》,现在我拉给他听,竹影里的声音能传得远”。菊园区更热闹,石桌上刻着棋盘,几个老人围坐着下棋,棋子落得“嗒嗒”响,其中一位指着碑说“老周,你这马走歪了”——碑上的老人笑着,照片里还举着副象棋。

守园的张叔在这儿住了十年,宿舍门口种着一丛月季,红的黄的开得热热闹闹。他的记性比账本还清楚:“第三排左数第五个,碑角刻着小太阳,是去年那姑娘画的”“第五排右数第三个,逝者爱吃橘子,你看那碑前总摆着橘子皮”。上周有个姑娘急得哭,说找不到奶奶的碑,张叔一拍大腿:“跟我来!”果然在梅园区第三排找到——碑角的小太阳被张叔用刻刀描过,比去年更清晰。张婶更贴心,在桂树底下摆了几张石凳,说“有人来早了,能坐会儿歇口气”,桂树是她和张叔刚来时种的,现在比人还高,风一吹,桂香裹着银杏香,飘得满园都是。
昨天下午,我看见个穿粉色连衣裙的小姑娘,举着纸鸢往银杏林跑,妈妈在后面喊“慢点儿”。小姑娘跑到最粗的那棵银杏树下,把纸鸢挂在枝桠上——树洞里塞着好多纸鸢,有燕子、蝴蝶,都是孩子们挂的。妈妈蹲下来,摸着树洞里的纸鸢说:“外婆生前最爱带你来放纸鸢,现在她在树上看着你呢。”小姑娘仰着头,纸鸢在风里飘,影子落在旁边的碑上,碑上的老太太笑着,眼睛弯成月牙,像在跟着纸鸢跑。
黄昏时风凉了些,张叔拿着扫帚扫银杏叶,把叶子堆在碑前的空地上:“留着给孩子们玩,去年有个小娃娃把叶子装在玻璃罐里,说要给爷爷送‘金色的星星’。”我捡了片银杏叶,脉络像老人的手掌,纹络里藏着阳光的味道。远处的二胡声又飘过来,是兰园区的老先生在拉《良宵》,琴音裹着桂香,飘过高高的银杏枝,落在每一块碑前——像有人在说“别急,我再陪你坐会儿”。

北京的秋天短,可佛山陵园的秋天很长。长在银杏叶的黄里,长在桂香的甜里,长在张叔的念叨里,长在每一个来这儿的人藏在心里的想念里。这里没有冷森森的碑群,只有带着温度的记忆:有人来读没写完的日记,有人来放亲手做的布偶,有人坐在石凳上吃橘子,橘子皮滚到碑脚,风一吹,像在说“我吃了,你也尝尝”。
傍晚的阳光斜斜照进来,银杏叶的影子铺在青石板上,像铺了层温柔的纱。张叔扛着扫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