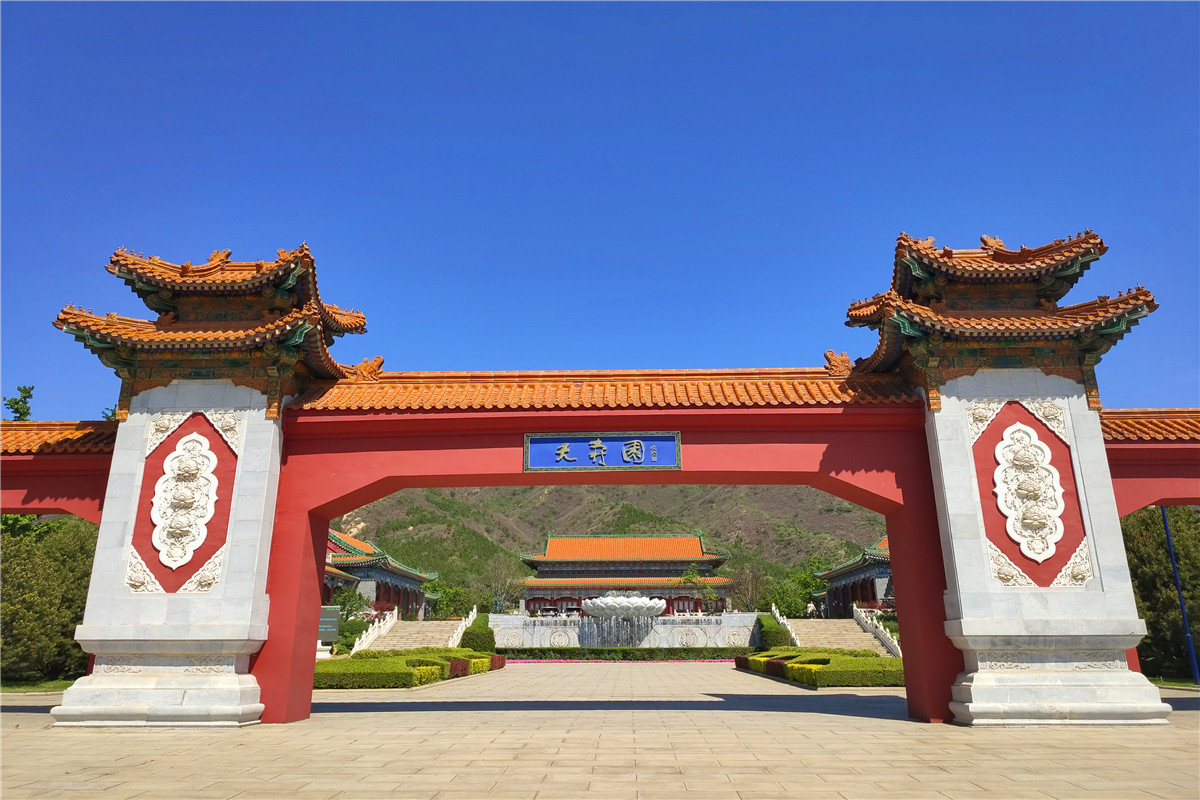风里还裹着点杏花的甜香,巷口的煎饼摊飘出焦脆的香气,我攥着温热的豆浆往公交站走——今天要去八达岭人民公墓,坐清明专线班车。
公交站的人比平时密些,大多手里捧着花:白菊的瓣儿沾着晨露,百合裹着透明玻璃纸,还有几枝淡紫勿忘我,像揉碎的星子落进花束里。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举着牌子晃了晃:“八达岭公墓的班车在这边排队!”我跟着队伍挪过去,前面的阿姨背着布包,包里露出半截折叠凳:“我每年都坐这班,师傅熟得很,去年清明堵在高速口,还是他打电话让我绕了条小路,才没误了给老伴儿摆花的时间。”
七点整,淡蓝色的班车稳稳停在站边,车身上“清明专线”四个字染着暖黄的晨光。司机师傅戴着鸭舌帽,先跳下来扶人:“老太太,您扶我胳膊,台阶有点高。”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,旁边的大爷抱着束白菊,指节泛着薄茧的手轻轻摸了摸花茎:“我老伴儿生前最嫌我买贵花,说‘能买三斤苹果呢’。去年我带了盆金边菊,她在梦里还跟我念叨,说我浪费钱——你看这花,是早市刚摘的,才五块钱一束,新鲜得很。”我笑着递给他一瓶矿泉水:“大爷,先喝口,路还长着呢。”
车启动后,沿着八达岭高速往山上走,路边的柳树抽了新芽,山尖还飘着层薄雾。司机师傅的嗓门敞亮得像巷口的老茶客:“您扶好啊,前面有个小坡!”话音刚落就慢踩了刹车,旁边的老太太扶着座椅背笑:“这师傅,比我儿子还贴心——上次我坐别的车,司机急刹车,我差点撞着前座。”车厢里慢慢热闹起来:斜对面的阿姨跟旁边人聊起去世的父亲,说他生前爱下棋,现在公墓的石桌旁还留着他的棋盘;后排的小姑娘举着手机跟妈妈视频,晃了晃手里的纸花:“妈妈你看,我给爷爷折的百合,比买的还好看!”

四十分钟后,班车停在公墓门口。司机师傅跳下来,帮着搬花:“您这花束沉,我拎进去——里面的台阶滑,您慢点儿。”旁边的志愿者递来一张印着二维码的地图:“ABC区扫码就能查位置,有需要喊我们,别客气。”我跟着大爷往公墓里走,他把花摆在墓碑前,摸了摸碑上的照片:“老伴儿,茶我泡了,还是你爱喝的茉莉,桃酥是老店里的,没放糖精——你上次说嫌甜,我记着呢。”风掀起他的衣角,花瓣轻轻落在碑前,像有人悄悄说了句“我来了”。
中午返程的时候,班车还停在原地,司机师傅在擦前挡风玻璃,帽檐上别着朵小姑娘送的蒲公英。志愿者举着矿泉水瓶喊:“累了的同志先喝口,车十分钟后走!”车厢里比去的时候静了些,有人抱着空花束,有人摸着口袋里的纸钱灰,司机师傅放了首慢歌,旋律轻得像落在花瓣上的风。我望着窗外的夕阳,把公墓的影子越拉越长,直到变成后视镜里的一个小点——那些没说出口的话,那些藏在心里的思念,都被这班车载着,从烟火里来,往烟火里去。
车进市区的时候,巷口的煎饼摊已经收了,风里还留着点焦脆的余味。我攥着空豆浆杯往家走,口袋里装着从公墓摘的一片银杏叶——去年清明也摘了一片,现在夹在笔记本里,边缘已经黄得像琥珀。路过便利店,我买了瓶茉莉茶,对着空气笑了笑:“阿姨,大爷没买贵,菊花是早市挑的,新鲜得很。”

晚风里,我听见远处的班车喇叭声,轻轻的,像在跟谁说“再见”。清明的雨没下,思念却像杏花的香,飘得很远很远。那辆淡蓝色的班车,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