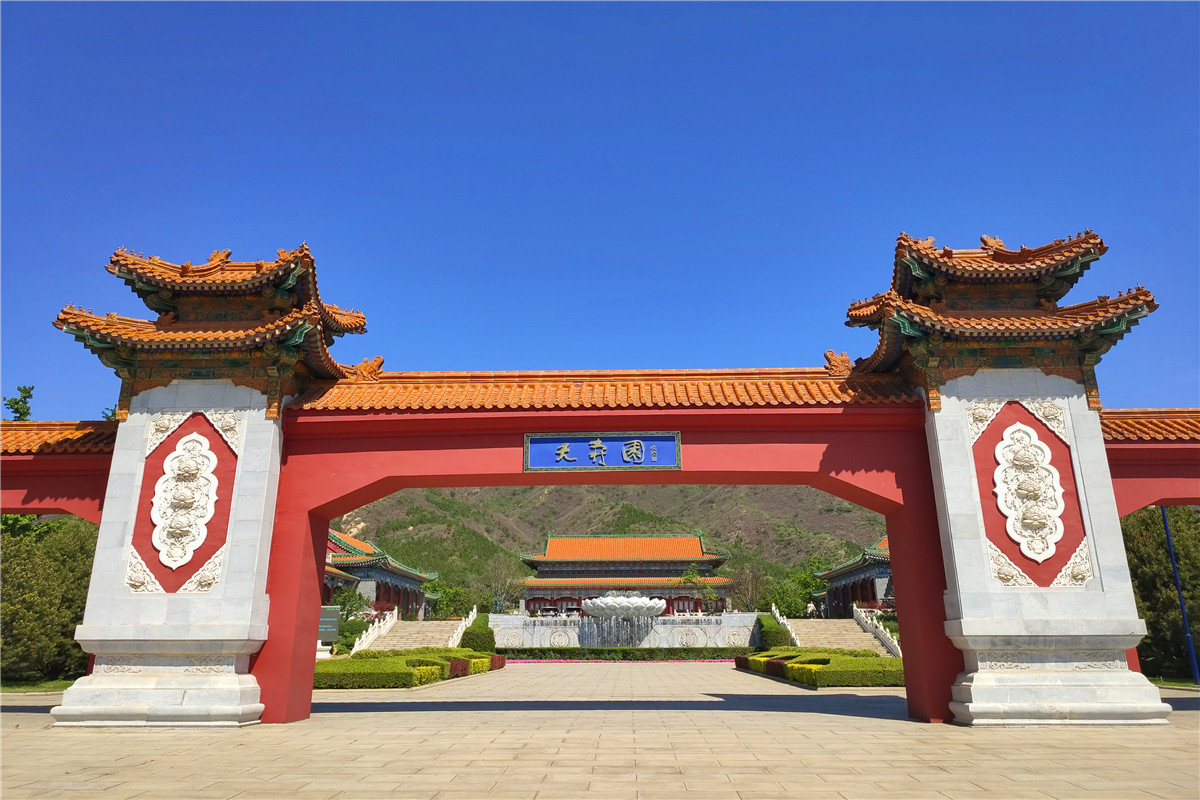清明前的风裹着槐花香钻进衣领时,我正跟着张阿姨往宝云岭的深处走。她手里攥着个磨得发亮的不锈钢水壶——那是她老伴生前用来浇阳台月季的。"第三排倒数第二棵国槐,你看树干上那枚铜牌,刻着他的名字。"阿姨的手指掠过槐叶,细碎的光斑落在她眼角的皱纹里,像撒了把温温的碎银。
宝云岭的树葬区没有想象中肃穆。没有整齐划一的墓碑,没有冰冷的石狮子,只有高矮错落的树——国槐的枝桠撑着绿伞,银杏的新叶像小扇子,侧柏的针叶挂着晨露,每棵树的树干上都挂着枚掌心大的铜牌。有的刻着"老周,爱喝茉莉花茶",有的刻着"小棠,再给妈妈唱一遍《小星星》",甚至有棵桃树的牌上写着"奶奶的腌萝卜,今年比去年咸"。工作人员说,选树要讲"缘分":喜欢养花的选月季树,爱听京剧的选国槐,总蹲在阳台看云的选银杏,每棵树都带着亲人的"小性子"。
张阿姨的老伴选了国槐。"他以前总说,老家门口的老槐树是爷爷种的,小时候爬树掏鸟蛋,被刺扎得满手血,还是要往上爬。"阿姨摸着槐树皮上的裂纹,像摸着老伴手掌的茧子,"去年清明来,这树才到我肩膀,今年都比我高一头了。上次刮大风,我急得半夜打电话给园区,结果工作人员说,早给树绑了防风绳——你看那根红绳子,还系着我去年挂的祈福卡。"她仰起脸,风掀起她的衣角,槐花落进她的发间,像有人悄悄撒了把温柔的雪。

树葬区的尽头有片小广场,木架子上挂着密密麻麻的红丝带。有个穿校服的小姑娘踮着脚系丝带,丝带末端挂着片银杏叶——那是她奶奶的树。"去年秋天,我捡了满满一书包银杏叶,夹在课本里。"小姑娘的眼睛亮得像星子,"昨天数学考试,我摸着叶子上的纹路,突然想起奶奶教我认数字的样子——她用银杏叶摆成1、2、3,说'叶子会长大,数字也会长大'。"旁边的工作人员凑过来笑:"这棵银杏是去年春天种的,现在都快两米高了。上周小姑娘来,说'奶奶的树比我长得快',非要量量树干的粗细。"

傍晚的时候,我坐在树葬区的石凳上。风里飘来槐花香,混着泥土的腥气,还有远处传来的鸟叫。张阿姨蹲在国槐树下,把水壶里的水慢慢浇进土里,水珠渗进泥土的声音,像谁在轻轻说"我在呢"。不远处,一对年轻夫妻正跟着工作人员选树——女孩摸着银杏的树干,说"就它吧,我爸以前总说,银杏的叶子像蝴蝶,等秋天落下来,肯定能飞到他的书桌上去"。男孩握着她的手,指尖在铜牌上轻轻敲了敲:"那就刻'爸爸的蝴蝶,落在银杏叶上'。"
宝云岭的夕阳落得慢,把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我望着那些在风里摇晃的树,突然懂了树葬的意义——不是把亲人"埋"起来,而是让他们"长"起来。当春风吹绿新叶,当夏蝉在枝桠间唱歌,当秋风吹落银杏,当冬雪压弯侧柏的枝,那些没说出口的想念,那些没做完的梦,都会顺着树干往上爬,藏在每一片叶子里,每一圈年轮里,每一阵风里。就像张阿姨说的:"以前总怕忘了他的样子,现在看这棵树,就像看见他坐在阳台浇花,阳光穿过槐叶,落在他的老花镜上,泛着光。"
风又起了,槐花落了一地。我捡起一片,夹在笔记本里。鼻尖萦绕着槐花香,像有人在耳边说:"看,那棵树,又长高了一点。"